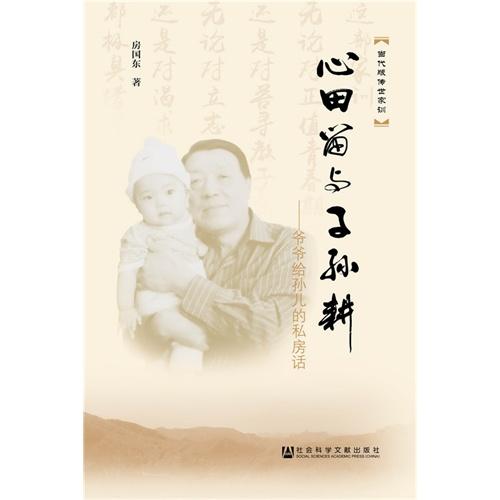著名作家耿曉麗|哭泣的玫瑰(小說)
更新時間:2023-08-27 關注:169
1半夏和半夏花
九月的云南玉龍小鎮(zhèn),細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
半夏姑娘拖著日漸消瘦的身體,從遙遠的北方村莊先是坐鄉(xiāng)村班車后又轉乘省城大巴,既而又在空中飛了一圈,一路輾轉,歷經(jīng)十多個小時,終于見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忍冬。
忍冬曾深情地說很喜歡很喜歡半夏姑娘的長發(fā),半夏姑娘俏皮地回應:“長發(fā)為你留,相思無盡頭。”忍冬還說喜歡半夏穿長裙的模樣,半夏癡戀地承諾此生為你穿羅裙,不分春夏和秋冬。此時此刻,半夏的長發(fā)淋濕了,貼在了臉頰,衣裙淋濕了,緊裹住嬌軀,手捧一束艷麗的玫瑰,一步步吃力地向他的忍冬走去。
不知是雨水遮擋了她的視線還是淚水擾亂了她的心緒,玫瑰刺眼的紅,半夏每走一步更顯得蒼白無力,十米、五米、三米、一……忍冬,對不起,我來了,你的半夏來了。
半夏跌跌撞撞地倒在了忍冬的墓碑上,額頭磕出了血,血在雨水的洗禮下滴在了玫瑰的花蕊,是雨在落淚還是玫瑰哭泣?“忍冬”半夏手顫抖著撫摸著墓碑上那張熟悉而英俊的照片,“忍冬,你的半夏來了,再也不會和你分開了,對不起,我不該對你說謊,我不該對你隱瞞,都是我不好,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夠幸福啊!忍冬,不,我的勁松,我好冷好冷,你說你就是一棵勁松挺拔駐守在邊關,為了一方平安你愿忍受冬的嚴寒。你說我就是你的夏天,是你生命中的另一半,忍冬你可否知道,半夏失去你就失去了人生的四季,我、我……”額頭、鼻孔、嘴角都溢出了血,對應著雨的白,顯得那么刺眼!
一輛軍車在玉龍墓地戛然而止,警衛(wèi)員一手給許政委撐著傘一手抱著一大束半夏花,這束半夏花可是許政委下了命令就是跑遍麗江城玉龍縣也要找到買到,實在不行就到昆明。總之一句話,就是要在今天看到半夏花。小楊到現(xiàn)在還不明所以然,不給忍冬哥帶菊花帶供品,費九牛二虎之力弄一把半夏花是何用意。
“小楊,快!快去看看怎么回事”。不知不覺許政委和警衛(wèi)員小楊已走到忍冬墓前一米處,小楊見狀。也顧不得手中那把許政委下命令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買來的花束,一把扔在雨中,三步并作兩步向墓碑跑去,當小楊俯身把倒在墓碑前的姑娘抱起來的一剎那,許政委震驚道:半夏姑娘,她是半夏姑娘,那個遠在北方的剛毅姑娘啊!
小楊還未回過神,許政委就命令:快,快把半夏抱到車上送部隊醫(yī)院!
云南邊防武警部隊醫(yī)院急診室內,嚴主任親自出馬量體溫、測血壓、聽脈搏、做心臟復蘇、打強心針劑,一群穿白大褂的醫(yī)生護士進進出出,不敢怠慢。就是普通患者也得竭盡全力救死扶傷,這是作為軍人作為醫(yī)生的職責,更別說是許政委送過來的這位姑娘。
屋外風呼嘯著,白色的建筑在雨中似乎飄忽不定,恍若天降之物。屋內一股消毒水味直撲口鼻。這一樓層的病房是重癥患者的房間。每個房間里都充滿著死亡的氣息,吊瓶滴答作響,仿佛在給每一位穿著條紋病服的人們的生命倒計時。死亡籠罩著白色的建筑,暴雨傾盆,屋外刷刷作響的雨聲又讓病房多了一分絕望的死寂。
窗外的風大了,雨也大了,偌大的病房外,是凌亂的腳步和刻意放輕的談話聲。醫(yī)生的神情漸漸露出窘迫。原因是眼前這個政委嚴肅的表情。“你說什么?半夏姑娘白血病晚期,這怎么可能呢!那個活蹦亂跳的北方姑娘居然危在旦夕”。許政委激動地對嚴主任咆哮道。“許政委,對不起,我們已經(jīng)盡力了,半夏姑娘時日不多了,看她還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嚴主任一字一句地說,“能推斷半夏姑娘得病的時間嗎?”這次許政委緩和了許多問。“從半夏姑娘的脫發(fā)程度叛定,應該有一年多了吧,而且一直在接受化療”嚴主任據(jù)實說道。“你是說半夏姑娘知道自己的病情了,她的長發(fā)是……”許政委說。“是的,她的長發(fā)是假的”嚴主任回答。
“政委、嚴主任,半夏姑娘醒了,一直在叫著少校的名字(忍冬)”警衛(wèi)員小楊說。
“走,快進去看看。”許政委、嚴主任一前一后走進半夏的病房。
許政委握著半夏姑娘的手慈祥地說:“丫頭,我是許叔叔,還記得我嗎?“許叔叔好,半夏記得記得”,半夏無力地說著又咳了起來。“許叔叔,你可不可以答應,答應半夏一個請求。”說著半夏姑娘試圖坐起來。小楊趕緊上前扶著半夏。“包、包,咳咳”殷紅的血又從半夏的嘴角滲出。許政委用紙巾幫半夏擦干凈嘴角邊的血跡,掉轉頭憋回在眼里打轉的眼淚說:“丫頭,說吧,許叔叔答應你”。
半夏從床頭柜的手提包里拿出身份證、戶口本,還有一年前醫(yī)院的診斷證明,說:許叔叔,求你帶我去忍冬墓前,求你為我證婚,我要做忍冬的新娘。許叔叔,一年前,我找到部隊,對忍冬殘忍地提出分手,是因為我檢查確診得了不治之癥,我不想拖累他,我知道,他知道真相不會扔下我的,我想他擁有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說了那些傷人的話,我說嫌棄他家里窮,嫌棄他的母親身體多病雙目失明,嫌棄他只是個邊防兵,嫌棄他給我在省城買不起房子,許叔叔,你知道我說每一句每一字的時候心里有多痛,其實,我什么都不嫌棄,我的家人也不在乎他的家境,事實上,我的家人已把家中房子賣掉要給我做嫁妝,父母說現(xiàn)在他們租房子住,等以后需要他們幫帶孩子了,就過來帶孩子做飯,還再三叮囑我孝敬善待他的家人,理解支持他的工作,關心體貼他的生活……可是,我卻查出得了絕癥,我不想成為他的負擔。寧愿他誤會我嫌貧愛富,見異思遷,也不想他被我牽連受累。
許叔叔,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嗎?后來,后來,他在執(zhí)行任務犧牲了,我真想隨他一起而去。可是,我不能,我想在我即將消失的生命里再對幾位老人盡盡孝心。所以,這一年多,除了不得已的治療時間在醫(yī)院停留,其余時間我就在河北、云南兩地奔波。
后來,我就央求爸媽幫我完成心愿,不要再把錢浪費在我身上,我用本來打算給我化療的錢治愈了大娘的眼睛,許叔叔,我知道我沒多少時日了,你就成全我吧,好嗎?半夏聲俱淚下地說明緣由。
“丫頭,不要再說了,許叔叔答應你,叔叔一直就覺得你是另有隱情,忍冬也曾對我說,你是難得的好姑娘,你一定是有別的事,哪不是你的心里話。都怪我,那次任務太緊急,沒有給你們時間搞清楚。要是,我換做別人去執(zhí)行那次任務就好了……”許政委拉著半夏姑娘的手哽咽道。
“許叔叔,您不要自責,怎么會怪你呢?那次任務本身就存在危險性,忍冬怎么會讓別人去呢?半夏姑娘嘴角露出一絲笑容欣慰地道。”
“丫頭,那次你和忍冬都……”許政委驚問到。“許叔叔,您放心,涉及到國家機密的,忍冬一字都不會對我透露,哪怕我是他的半夏,他只是對我說,不管生與死,不管我對他說了什么,他都不會放棄對我的愛,她讓我在北方好好等著他,這次,如果任務完成,就提出退役,往后余生陪我一起,如果不幸離去,要我好好的,要我每年在他的祭日能夠陪他說說話,可我卻殘忍的對他說,要么你就現(xiàn)在跟我回去,給我在省城買房子,要么就此分開。他說,現(xiàn)在不行,這次任務很緊急,他不想領導和戰(zhàn)友為難,我就說了那些傷人的混賬的話,說誰稀罕他,不就是一個邊防兵,是給我買不起房子推塞吧?就這樣,他依然選擇的是留下來,配合戰(zhàn)友執(zhí)行任務。都怪我啊!都怪我,我就不該對他說這些,他心里是不是有負擔,他是不是分神了,才會中槍的啊?”我泣不成聲地說。
“丫頭啊!忍冬果然沒有看錯你,在執(zhí)行任務出發(fā)前。他們幾個一一向我告別,承諾保證完成任務,而忍冬額外地說:“他會為了他的半夏活著回來,請領導放心。如果,我萬一不幸犧牲了,請領導每年在我的祭日給我送把半夏花,北方太遠,他不想半夏每年長途跋涉的來陪他”許政委娓娓道來“后來,在他中彈送往醫(yī)院的路上,還斷斷續(xù)續(xù)的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半夏,這次真的食言了,不能去北方陪她了,不能在省城給她買房子了,他說,他就在南方,就在你們相識的那個小鎮(zhèn)等你,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娶你做新娘。希望,來生……”“許叔叔,忍冬真的這樣說的嗎?忍冬真的沒有怪我嗎?”半夏激動地搖著許政委的手說。許政委重重地點了點頭。
在這一刻,風停了,雨也停了,醫(yī)院里也聞不到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了,有的是玫瑰的馨香芬芳。
“許叔叔,我真的不是嫌貧愛富的姑娘,我對忍冬說的話都不是我的心里話,我是自私地希望他離危險少一次機會,離危險遠一點,我了解他,心想就賭一把,如果他真能陪我回家,我生命的最后有他陪伴,今生也無憾了。可是,咳……咳……我也知道他是不會把危險留給別人的,這也是我最欣賞最愛他的地方。至于,至于,咳……咳……我說的他就是一個邊防兵,您知道我說這句,心有多痛嗎?其實,邊防兵在我心里是多么神圣偉大啊!咳……咳”半夏激動地說著,不停地咳著,嘴里一次次咳出了鮮血。
許政委看向嚴主任,嚴主任無奈地搖了搖頭。
“小楊,立即通知下去,婚紗、化妝、攝像一個都不能少,還有把婚車以松葉和半夏花來做,手捧花要用丫頭帶來的玫瑰”說著看向病床上臉色蒼白的半夏。半夏會心的點了點頭。“老嚴,你這里抽調一支醫(yī)療隊前往陪同。”許政委轉頭對嚴主任說。“好、好,我這就去安排”嚴主任說。
“天空飄起了雪花 心里面好想他,這些天你過得好嗎?你可知道我的牽掛”半夏設置為雪花的手機鈴聲響起,半夏緩緩地睜了一下眼睛。許政委就勢從床頭的手提包里拿起手機說,丫頭你先睡會,叔叔幫你接。
2生死之戀
半夏手機屏幕上來電顯示“媽媽”,許政委遲疑了一下,還是接聽了電話:“好,好,老嫂子,你和老哥等著。我這就派車去機場接你們”。“小楊,你去機場接半夏爸媽,通知部隊所有官兵半小時后必須到達忍冬墓地。”許政委說到。
在救護車上,半夏身穿潔白的婚紗,假的長發(fā)及腰,佩戴著鑲有珍珠的美麗頭紗,蒼白的臉龐盡管已撲了粉化了妝還是忍不住人見猶憐,蒼白的嘴唇在唇彩的涂飾下楚楚動人,手臂上扎著的針頭,是那么的刺眼。“咳……咳”陪同護士忙用棉簽擦拭著半夏的嘴角。半小時后,當許政委的車子在通往墓地的甬道停下,隨即嚴主任陪同的救護車停下了,小楊接半夏爸媽的車也停下了,部隊官兵的車輛停下了,從忍冬的墓碑到所有車輛停駐的道路,一盞鮮紅的地毯鋪落開來,那是和忍冬并肩作戰(zhàn)出生入死的兄弟,在為他們親愛的戰(zhàn)友鋪設一條幸福的路。
墓碑前,忍冬媽媽在女兒的攙扶下,顫巍巍地向紅毯的一端走去。
“丫頭,叔叔帶你去見忍冬,你準備好了嗎?”許政委扶著半夏姑娘道。
“許、許叔叔,我,咳……咳,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走到忍冬面前的。”半夏無力地說。嘴角除了殘留的一絲絲血跡還有幸福的笑容。
“閨女,你嫁這么遠,以后就不在爹身邊了,讓爹背你到忍冬面前好不好?”半夏爸爸眼里含著淚說。
“是啊是啊,你小時候最喜歡粘著你爹背你了”半夏媽媽也附和道。
半夏無力地點了點頭,在許政委和小楊的攙扶下爬在老爹爹的背上,頭無力地垂在老爹爹肩上,老爹爹眼含著淚花,他的丫頭現(xiàn)在骨瘦如柴,頂多也就80來斤,可老爹爹卻感覺像一座山壓過來,艱難地挪動每一步,隨著他腳步挪移,半夏的媽媽抹著眼淚、許政委抬頭強忍住淚水、小楊醫(yī)護人員早已淚流滿面、部隊的戰(zhàn)友邁著整齊的步伐,從兩旁走開到忍冬的墓碑前迅速散開成心形的隊形,墓碑前也整齊有序地用松枝和半夏花合圍成一個心形,正中有個空隙,等待半夏親手把那束玫瑰放在那里。
忍冬媽媽在女兒的攙扶下,迎上了半夏的老父親。許政委趕緊上前抱半夏姑娘在懷里,“丫頭啊,你咋這么傻啊?讓我老婆子好好看看你,你把自己照顧好啊,你為什么為我這瞎老婆子花錢治眼睛呢?”忍冬媽媽說著,從女兒手里接過錦盒打開,取出鉆戒戴到半夏的左手指上,“丫頭,這是冬兒早就買好的,說給你戴上了,你就是他媳婦兒了。這輩子就別想再逃離他了。今兒個我把它代冬兒給你戴上,希望你們下輩子還要在一起。”“嫂子,謝謝你出錢支助我上大學,我一定會好好學習。不辜負你的善良”忍冬妹妹拉起半夏的手說。
半夏輕輕地叫了聲:媽、妹妹,對不起,我這次可能真的不能替忍冬照顧你們了!對不起!邊說邊走向忍冬的墓碑。
人生若只如初見,所有往事都化為彩云之南的一場煙雨,在相視一笑中,隨風蕩漾起回憶的波紋,然后再漸漸隱去在畫中的玉龍雪山,只因為你的離去,我竟為你傾情傷懷,從北到南,又從南到北,每個365天!
跪坐在忍冬墓碑前的半夏,纖細的手撫摸著墓碑上忍冬的照片,笑著哭了,哭著笑了。思緒飄飛到那個曾經(jīng)初始的麗江機場……
半夏從貧困農村到都市求學的幾年,歷經(jīng)悲歡離合,畢業(yè)后一路輾轉,還沒有從大學生活的噩夢中醒來,初到云南便經(jīng)歷了驚心動魄的一幕:半夏的背包里被毒販神不知鬼不覺塞進去“冰毒、嗎啡、可卡因”2000克,“抓住他,抓住他,不許動”幾個穿著便衣的邊防緝毒警察在半夏的周圍一涌而上,瞬間,機場出口大廳喊聲、哭聲亂成一片。半夏也誠惶誠恐地閃到一側,突然感覺有一絲微涼抵在脖頸處,隨之頭發(fā)被手臂上有一道疤痕的瘦小男子扯著,“不要過來,你們都退后,把槍放下”疤痕男子對著圍上來的緝毒警察喊道。“都退后,把槍放下,一定保證人質的安全,”忍冬對著一起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說,并對疤痕男道:“放開她,我換做人質送你安全離開這里。
“放開她,怎么可能?有她在我手里,我才是安全的,快給我退遠一點”疤痕男對著忍冬咆哮道。
“哈哈哈,我在你手里你是安全的,這真是我聽到最大的笑話,別忘了你們做的好多事情都在我的手機視頻里,你以為在機場我們只是萍水相逢嗎?告訴你,我已經(jīng)跟蹤你們很久了,包括你的住所、行蹤、計劃都了如指掌”半夏姑娘不卑不亢的甜美聲音響起,使得疤痕男和幾名執(zhí)行任務的緝毒警察都很驚訝。
疤痕男伸手去搶半夏手中的手機。半夏說時遲那時快,隨手把手機拋向忍冬的方向,疤痕男見狀立馬放開半夏,跑向忍冬爭奪手機,借此機會,半夏迅速地跑向另一側的緝毒警察身邊,“砰砰”隨著槍聲響起,疤痕男雙膝跪倒在機場的廣場,這時,忍冬走向半夏,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并用帶有本地口音的普通話說:謝謝你美麗勇敢的女孩,手機還你,那個……那個,我剛剛把我的手機號碼存進你的電話本當中了,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說完,忍冬轉身離開。
此時,疤痕男已被另幾名緝毒警察押解著向廣場外的警車走去。
在北方生活的半夏,習慣了四季有落差的氣候,初次來到四季如春的城市,一時有點不適應。在北方已步入初夏,半夏身著一襲長裙,然而,在飄著絲絲縷縷小雨的春城,剛剛經(jīng)歷了膽戰(zhàn)心驚的一幕,此刻,半夏感到了微寒。想想行李箱里,都是薄薄的裙衫,倍感春寒料峭。半夏抱緊雙臂,漫無目的地行走在雨霧里。
與此同時忍冬一行人駕乘的警車也行駛在雨霧里,透過倒車鏡忍冬看到了一個無助的身影,模糊又清晰。
“靠邊停車,你們先行,我隨后趕上”忍冬對駕駛警車的戰(zhàn)友說。
“我想在綿綿細雨中漫步,不穿雨衣,不打雨傘,任雨淋濕我的發(fā),我的眉,我的眼,只渴望頭頂會突然撐起一把傘,一雙大手摟住我單薄的肩。”這是半夏姑娘曾在日記中寫到的句子,而此時此刻,她更想在暖暖的家中,想著暖就越發(fā)地感到冷,這時半夏想到了背包里還有一件長袖的防曬衣,不奢望能夠遮風擋雨,最起碼是長袖的,心靈上可以有些許的慰藉,半夏姑娘蹲在一邊把背包摟在懷里,拉開拉鏈,正要取出衣衫,不料,包里一些包裝不同,大小不一的東西使其更加冷得發(fā)抖。這時候突然雨停了,半夏姑娘不由地抬頭望向天空,哪里是雨停了?一把迷彩的傘撐在了自己頭上,而撐傘的正是那個要做人質交換自己的緝毒警察。“很冷吧?這樣淋雨會感冒的,來,我送你回家。”忍冬夾雜著本地口音的普通話再次響起,很是好聽。
“謝謝你,”半夏抱緊了背包,環(huán)看了一下四周繼續(xù)說“我正好有事對你講。”“好,你家住哪里?先回家換了衣服,有什么話回頭再對我說,這樣穿著濕衣服,真會感冒的”忍冬說。
“我第一次來麗江,麻煩你幫我附近找個酒店吧!”半夏怯怯地說。
“哦,那好,前邊不遠就是機場居家酒店了,走吧!”忍冬柔和的安慰半夏道。
“忍冬,你生前最憎恨毒品,而你也說過我就是你的彼岸花,像罌粟一樣殘艷,會讓你上癮,會讓你瘋狂,會讓你愛到無法自拔,忍冬,你醒過來,醒過來愛我啊!愛你的彼岸花啊!”半夏纖手撫摸著墓碑上忍冬的照片哭泣道。不由地思緒又回到初始的那個雨天……
半夏是如此信任忍冬。把背包里被毒犯放進去的毒品全部交由忍冬處理,忍冬看后對半夏道:原來疤痕男子控制你不單單是做人質離開這里,他更惦記你背包里面的東西,一旦離開,他就可以成功轉移,你太機智勇敢了。謝謝你!
“忍冬,我蔥蘢的勁松啊!我心愛的曼陀羅啊!你的彼岸花來了,我們再也不會分開了……”咳咳,咳咳,殷紅的血順著嘴角滲出,滴落在潔白的婚紗上,吹生命一池漣漪,秋風莫逆。千年不渝的夢終化作斑斑殷紅的浮萍,不勝風雨。此刻一陣狂風卷來,帶來了驟雨,驟雨抽打著地面,抽打著墓碑,雨水淚水橫飛,迷蒙一片。許久,風漸漸停息了,雨也小了下來,像絹絲一樣,又輕又細,聽不見淅淅的響聲,也感覺不到雨澆的淋漓。只覺得好像這是一種濕漉漉的煙霧,濕漉漉的沉重,壓得所有的人喘不過氣來。
“花、花”,半夏微弱地說道。小楊趕忙把那束半夏花遞到半夏手里,半夏把半夏花插在玫瑰花束的中間,輕輕地放在心形的中間,隨著一口殷紅的血噴在花束上,一滴清淚也順著臉頰滴落在花束上,半夏會心地笑了,笑著笑著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所有參加忍冬和半夏婚禮的人站在雨里,像泥塑木雕一樣,一動也不動,好像在每個人的心上面系了一條繩子,走一步,牽扯一下,牽得心陣陣作痛。玫瑰的花朵看了凋殘了,半夏藥草聽了枯萎了,它們都在哭泣啊!眼淚在所有人的眼眶里打轉、打轉……
三年后,云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白沙鎮(zhèn)的一家農舍院落里,院墻外勁松挺拔,墻內半夏花開得正艷,芳香四溢,一對孩童正在采摘半夏花草,小男孩稚嫩的童音說:長大了,我要當一名邊防緝毒警察,像舅舅一樣,保家衛(wèi)國為人民服務。小女孩則調皮地說:我要當一名作家,寫舅舅和舅媽的故事……走嘍走嘍!小南小北把你們采摘給舅舅、舅媽的花束帶上,忍冬妹妹攙扶著老母親帶著一對雙胞胎孩童走向墓地……
作者簡介:耿曉麗,女,80后。筆名彼岸花、晨曦,就職于河北省阜平縣電視臺。中華詩友會理事兼河北分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河北省文學藝術研究會文旅采風委員會副秘書長、阜平文旅采風團團長兼秘書長、魯迅文學院保定作家班學員、保定市作協(xié)會員、漢中市赤土嶺文協(xié)微信官網(wǎng)駐站作家、“南國文學”優(yōu)秀主編、第五屆中國當代實力派優(yōu)秀作家。在國家、省、市級刊物雜志發(fā)表文章多篇,并多次在全國征文大賽中獲獎,出版散文集《彼岸花開》、小說集《只如初見》,創(chuàng)建公眾號“青檸書鳶”文學平臺。
-
·陳才生 | “老樹新花,故紙新畫”——談王興舟的讀書觀2024-08-27
-
·詩意人生的感悟與吟唱2024-08-30
-
·【視界晨報】“尋福記”名家漂漆書法與植物畫非遺作品展在福州成功舉辦2024-08-25
-
·陳寶璐|于最美的秋天里,收獲歲月的深情(美文)2024-08-25
-
·瘦石先生詞十首2024-08-22
-
·【實力派作家】屈光道|谷雨云詩六首2024-08-22
-
·河南安陽:殷都區(qū)人民醫(yī)院中醫(yī)科開展“中醫(yī)科普大講堂”活動2024-08-21
-
·【視界晨報】熱烈祝賀孫喜民被山東省散文學會吸收為會員2024-08-20
-
·【視界晨報】李士文|詩詞三首2024-08-20
-
·【視界晨報】安陽仁康精神衛(wèi)生專科醫(yī)院慶祝第七個中國醫(yī)師節(jié)活動2024-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