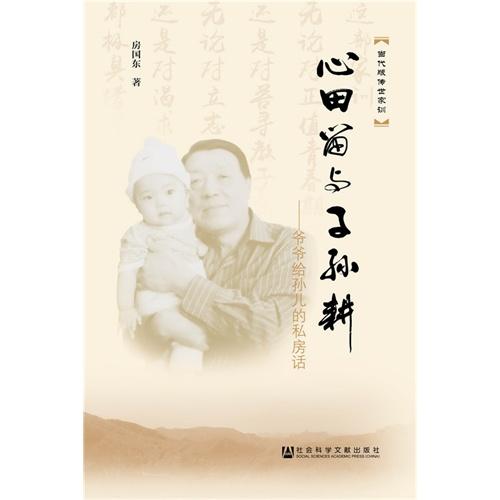【王志嬌】盲
更新時間:2020-05-06 關注:134
文/王志嬌
月亮不會無處不在,所以創造了六便士。
文學舉目似乎頻繁渴望撕心裂膽的灼痛,我想著,只要有扶住精神的器皿,眼睛也不過為參透痙攣的軀殼,縱使一灘崎嶇,滿河腥血,可春終究是春,嘴里嘴外含著利器,即便在利欲熏心中散去了光明。
若沒有六便士,月光也將失去太陽。
你可知,盲人的胸中涂有數不盡的白,有消融的積雪、深情的冰層和海鷗振翅翔集的雙肩,有稀釋離愁的歌調和河水撞岸的不落窠臼的嗣音,甚至踏足歸天的往來哀笛與不言而喻的青春吶喊,有雄踞九州同響的烈酒,亦有泯滅筆桿的沉淪;選擇孤行或則合眾,都伴有肆意流淌的高雅,那超凡脫俗,那起死回生的誓言與來自太平洋彼岸的渡船的號角,不正是熏黑眼球對白詩的誦吟?
長此以往,逝去的挽歌,使我的眼瞼成了永遠無法在春天歌唱的亡魂。時代茍延殘喘,現實一身空洞,沒有珠光寶氣的鮮艷、濃妝艷抹的妖嬈,亦沒有田間作壟的鋤把和拴住夕陽的牧羊人所驅趕的米色羊群;后來,我學著與粗糙的松花湖言和,握住的竟是水花萬盞與浮萍金藻,這深藏在萬物宿主間的多情,猶如自然的相睹相融,林立依賴。憶往昔,拾不起的曼妙鄉音,亦伴著芳草如茵的村落和草丘,與邊陲小城徐徐燃燒的煙塵一起,橫亙在任何發聲的眉宇。我思索著,假以時日,自我靈魂大不必再向那一串串冰冷的數字殫精竭慮,而是憑心感活——我自寒冬而來,在欣欣向榮的狗吠中鎮定昂揚,我敢于虧欠,也敢于彌補;敢于撼動,也敢于憑一筆之力遏制民不聊生的戰亂。
多少寄予厚望的春天,多少遠方相通相牽,人的一生,究竟要花多少時間糾纏于睡夢中,白白犧牲,我不甘心,執意醒著,卻愕然發現以此依舊走不好腳下的路。再去尋那生物鐘時,天已不暮將暮,我酒至半酣。卷翹的睫毛似也混沌不開,盤算著新的須臾又要在重蹈覆轍中接近尾聲,可我,烏漆漆的盲者,始終一個人,睡不沉,醒不來,亦愈發滄桑憔悴。
我看不到月光,可心還仍舊亮著;我只想關心活著的人類,如何繽紛任性,揮霍光陰。我憑嗅覺奔走大地,借觸覺撫摸人間,我還有一雙聽盡善惡的耳和極度嗜醉的饞蟲。盡管這是我的一切,可土葬之人,拜別天際時所能攜帶在身的,又能多于我幾重?
兜了一雙瞳孔?視錐層或許睫狀體?抑或是美其名曰視網膜的“救命稻草”?不論多遠,多短暫,他的肩膀固然于我要沉重些許,不也同樣生而為人,繼而演匹夫,為人夫,為人父?不也同樣日日負責推開生活席卷而來的波浪,扛起文字的課本,從啟蒙三年級至畢業五年級,從青春攬夢至婚姻嫁娶,一個一個幸福的結點,一個一個不問歸期的離難,一個一個如浮光掠影,雖出生入死,卻默默無聞;雖壯闊凌厲卻更加銹漬斑斑;雖身處文學的僻壤窮鄉,也難免悠然酸楚,卻寧可一生醉人,也永不凋零、視若無睹,人類啊,何必遺憾生命本不能的表達!
歷經一路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便循規蹈矩,輾轉四月。于不經意間,我捕到一縷泛濫褶皺的火苗,捋著淡淡惆悵的醉氣,一位蹣跚老翁正以吹壺煮酒。其身旁的閑庭梨渦長而又深,我只悟到一琴一瑟的喘息彌之和暢,竟未知,那白得發狂的語調亦優雅難尋。
“為何煮酒?”我認真地問。
“酒濁——溫酒。高沸呼為煮;現炭基以燃,微火溫之。”
他故作糾正,繼續與我周璇:“逢酒必煮,充饑,藥用,兩全其美......奧,不是酒,是藥!”皎潔的笑揉碎在淺云里。
“藥?”我近乎狂躁。
“醫什么?這酒凄寒無比,可心是熱的,以心溫酒,苦澀的寒氣才能自唇邊蒸騰而出,我聞過。”我只顧據理力爭,絲毫不求妥協。
“醫——神。”
“卻原來,酒不論冷暖清濁,亦藏匿著為人、習文之道。若有人中途‘眼疾’,應令其煮酒去病;若藝術行將失明,則理當同樣煮酒嗅醉。即或討不得諄諄教誨,倒不如換得一時透徹清靈。”
斯時,他轉過身來,放慢了語氣,看看發呆的我,又掂掂酒,一笑一顰,情有獨鐘。
我挺起頭顱,偽裝清醒,勉強證明無畏與其對抗的勇氣。
“非沸不能清其味,非登峰不能享其生。熘過而先熱,飲過而后熟。如苦酒不苦,是心欲使惡,那成就西蜀半壁江山的劉氏,最懂這溫酒的甘醇,也自然明了這“泉眼”自染上凡塵俗癮,往往會一改“故轍”,而異常鏗鏘、辛辣至極。如今你眼盲,是當真看不見?”
我愕然,抓濕了手中唯一的銀幣。
“是啊,此刻不妨捫心自問:自己努力掙扎這么久的結果,就是衣食富足,僅此而已?既然如此,那內心最終的自我索求又在哪?古往今來,倘或事物真正重要,只無需窺見,便心知肚明,那......是硬幣狹隘了我,還是我狹隘了文學?文學?一個永遠不會返回、亦永遠不會老之枯竭的稱謂。”似“非”而“是”,所言如此。
待我通曉之時再去尋覓,老翁與熱酒竟已消失不再,眼前漫卷的是總也遲到的西洋梨花,那靚艷風露,素月決然,如靜女般不染半滴風塵的純貞,也曾婉拒了多少詩人風雅頌的筆墨紙硯。自那歸來,我也時常伴梨花佐酒,卻再也無緣邂逅那冰魂玉膚、剛柔并濟,“孤芳忌過潔,莫遣凡卉妬”,靜瞻那翌年嫣然,含煙帶雨,想著有撲鼻憐人的香氣,錯亂之際,怎一個純粹了得!綿綿幾時,車水馬龍獨占枝頭,泥鹽才下眉梢,酒醋卻淹上心頭,欲語還休。
彼時,耳畔響起春柴拉扯的酒花,好似以往歡騰歲月泛漲的譏笑,令囊括大地的盲眼起死回生,老翁的溫酒似是有意提點:我不熱愛硬幣,但必然途經。少年意氣風發,向著那白月光,而求成者急功近利,嘴角歪斜地撿起六便士,輕蔑而過,等蓄滿肚子歸來時,才發現,天已破曉。月亮是常活常新的“心靈窗口”,是與時俱進的凡塵之眼,它和本能的生命截然不同,它將催促著你,永不停歇。我自幼讀不懂文學,文學排斥著錢權,錢權讀不懂我,我亦堅持著并不經濟的文學。目若舟楫,雖死猶存,當欲望開始失明,清酒定已扶不起一顆塵心,在一語成讖之前,窮盡時間思索某一超我的何去何從,不正是文學天地里如謎一般的真相?
我是于腥風醎雨中飲醉的盲人,聚聚裂裂,不加拼湊,索性本本分分地醉在路上,結結實實地表達想要呈現的城市與村莊,我想向往,像兒時一樣,不曾將英雄與拯救摻雜其中。硬幣與月亮之間的隔膜與荒謬地帶,幾乎人跡罕至。大道至簡,我只知不應對時代無可奉告,而只心無旁騖地展露拳腳,哪怕物欲橫流,七七八八,哪怕寇敗王成,空無所傍,也一定如愿以償。
時過境遷,苦旅漫漫,也許我所堅定的、鏖戰的、沉迷的、畏懼的......拮據到一輩子都無法企及,但冬去春來,隨手挽起的婉轉與動聽呵!五光十色的春天又何止你一個?
悄然擱置對文學的偏執,我曾終日碌碌無為,以丑示人,卻也樂在心頭,不為外在所累。
文學以外的利益糾葛,一如根牽著梗,梗栓著葉,日日耀武揚威,愈發不著邊際。我曾嘗試分裂,將完整的忠心均衡分配,但山崩地裂和肝腸寸斷的片段與日俱增,而后,是兩個我,三個我,四五六個我的惡戰。偶爾聰明,偶爾果斷,偶爾嫉惡如仇,偶爾惡語相向,什么都包括,什么也都除外,我學不會向月光撒嬌,因此也錯失了很多相互示意的美好。
我也曾勤懇地將右手伸出窗外,摸了一晃而過的沽名與半斤薄利,久而久之,便再沒清醒。路人問我,握住了什么?某一日,若將其送至當鋪當了去,錙銖必較間又能販賣多少珠寶金銀?
如今布袖也患上油的泥腥,我曾試圖放蕩自我,在如柔毯一般的云端暢想:看不到月亮,那人類想握住的東西究竟在哪?
那紅樓一幢,是夢還是現實?是依水而制抑或和泥可鑄?
我吹著彩霞,哼著花生米,學天狗兒把月亮裝裱成銀幣的框架。
??? 我像一支云彩,體悟著生疏的人生經驗,從夸父的腋下輕盈而起,舉著無垠而遼闊的篷頂無動于衷;我難忘熱血與鐵性的青蔥檄文,企圖以一支湯匙把澄澈攪渾。倘若我是一枚硬幣,是不是要比你們種刻腦海的還要矮小或昂貴?倘若我是一劑白月光,會不會將比你們仰望的還要荒蕪?
那照遍六便士孤床的月光原形,而今安在?是黛玉、襲人還是寶釵、可卿?
那所透支我的是文學?是精神?
?我本以為,文學的本質即為本我發聲,就好比文人獨自定居荒野的照明行囊,銀幣孕育以食糧,精神鏤刻成風景,二者慢慢雜糅,鬼使神差而又理所當然地朝內心的月亮許愿。其實不然,人應分別而活,有各自熱愛的厚度和章法,活生生的,有血有肉,靈魂才不至于無處安放,個中形形色色,盲者又怎能例外?
想來,是文學接納了六便士,不論卑鄙與高尚、毒惡與善良、仇恨或熱愛、眼盲或非盲,皆一應俱全且互不排斥地并存于文學的錦囊當中,相比于俗世的藩籬,二者棲宿不同,判若云泥,亦獨循所奏。
“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梨樹的花瓣因月而襲,如同銀幣上亦能泛起苞芽。夜晚,讓四月的和煦吹進我柔軟的書房,我無感做六便士的主人,亦不一定摘得星辰,我只如饑似渴地在月光下行走,哪怕稱不上半個盲人,也要一直一直,不倫不類地,做個月亮與六便士之間的第三種人。
-
下一篇:【趙永富】記憶中的碾子房
-
·陳才生 | “老樹新花,故紙新畫”——談王興舟的讀書觀2024-08-27
-
·詩意人生的感悟與吟唱2024-08-30
-
·【視界晨報】“尋福記”名家漂漆書法與植物畫非遺作品展在福州成功舉辦2024-08-25
-
·陳寶璐|于最美的秋天里,收獲歲月的深情(美文)2024-08-25
-
·瘦石先生詞十首2024-08-22
-
·【實力派作家】屈光道|谷雨云詩六首2024-08-22
-
·河南安陽:殷都區人民醫院中醫科開展“中醫科普大講堂”活動2024-08-21
-
·【視界晨報】熱烈祝賀孫喜民被山東省散文學會吸收為會員2024-08-20
-
·【視界晨報】李士文|詩詞三首2024-08-20
-
·【視界晨報】安陽仁康精神衛生專科醫院慶祝第七個中國醫師節活動2024-08-19